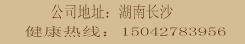我输给了时间
时间创造了我,时间赋予了我一切,我却输给了时间。
时间行至6月22日下午,医院病床上的我,鼻孔吸着氧气,右手挂着点滴,胸脯上吸附着多个电极,电极通过导线连接着心脏监护仪,心脏监护仪显示屏上走出均匀的波浪线。这种波浪线告诉我,这是心脏在跳动,证明我还活着。
我本来就活着,并且活得好好的,这是我自找苦头,没病找病!说对了,是在找病,准确地说是在找病根,找病源。
五月下旬,回老家小县城办事,巧遇单位退休老人开始体检,这样的机会我怎么可能放过?
几天后,体检报告单出来了。我打开粗略浏览了一眼,见“综述”和“诊断及建议”页面上罗列了一大串问题,两页A4纸写得满满的。见多不怪,我并不感到意外,近几年的体检报告单哪一年不是罗列着一连串问题?像“甘油三脂偏高”、“完全性右束支传导阻滞”、“肺结节”、“甲状腺结节”、“两肺气肿”等等,这些全是我熟悉不过的词眼,也就是说这些毛病早是我身上的“常客”,我对它们早已不屑一顾。
当我发现两点新情况时,内心不淡定了。觉得我身上已经埋下了地雷,随时都有被引爆的可能。
所谓两点新情况分别是:“左前分支传导阻滞”和“右侧颈动脉斑块形成”。我睁大眼睛,仔细盯着这两句话。心想:我眼花了多好!最好把这几个词看错了!
我揉揉眼睛,再仔细看,千真万确,一字不差。
记得前几年医生曾经对我说,“完全性右束支传导阻滞没有问题,不会影响心脏的正常工作,人的心脏血管只要左边的一条血管不要阻滞就行。”
医学上的遣词是非常严密、非常准确的,“阻滞”这一词无需查词典,我还是可以理解其中含义的。
能理解词的含义又有什么用?还不是听医生的,医生说“阻滞”没有问题就是没有问题,——因为他是医生,——是有专业知识的。
凭自己对自己身体的感觉:“完全性右束支传导阻滞”确实应该没有问题,因为我没有感觉到心脏有什么不舒服的,或者有什么症状的出现。
既然医生这么说了,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,就不把右边血管“阻滞”当一回事了,可是,我始终记清楚医生后半句话“左边一条血管不能阻滞”。
现在见“左前分支阻滞”一词,令我打了一个寒噤,心想:完了!不能阻滞的左边心血管也阻滞了。我再把“右侧颈动脉斑块形成”结合起来考虑,说明我的血管壁已经凝结了血栓,心脏血管阻滞的元凶是血栓,是血栓在作祟。血栓是个魔鬼,是个狰狞的夺命魔鬼。
心脏血管凝结着血栓真是个要命的东西,这确实是一颗定时炸弹,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。虽然现在感觉不到有什么不祥征兆,这才是最危险的征兆。许多人都这样说。
我拿着“体检报告单”去找体检主治医生。主治医生建议我做进一步复查。
我没有听从体检处医院复查的建议,而是带着“体检报告单”回到杭州。
在我驻地的附近,医院,医院,在当地还是颇有名气的,擅长治疗心血管疾病,刚好与我的症状对口。医院有一个专治心血管疾病的专家团队,医疗设备也是很一流的。
一大早,我空腹来到医院,挂了一位心血管内科专家号。专家医生看了看我的体检报告单说:“你这个年龄段的,是该复查一下”。
医生给我开了两张检查单,一张是“二十四小时动态心电图”,一张是“冠状动脉CTA”。
CT是什么意思,读者都清楚,至于CTA是什么意思,读者未必都知道,当然,医生除外。其实,叫我用专业术语解释CTA那是不可能的,因为我不专业,我只能用我的亲身经历、亲眼所见向读者描述一下,让读者自己去想象了。
CTA的医疗器械应该跟CT器械一样的,只是做CTA的患者要提前半小时在手腕上注入药水,并且在手腕上留下滞留针。
当我躺在CT机内,按照设备里的喇叭提示:做着“吸——气,憋——气”的时候,药水会自动从我右手腕的滞留针里注入到我的血管里,药水迅速流遍全身,一股热浪从脊椎和屁股上翻滚、升腾,好像要把我整个人掀起来一样,幸好医生事先跟我说过,心里早有准备,否则我会误认为我背下着火了,会从CT机内弹跳起来逃跑了。
这场“火”在我身上烧起又快又猛,灭时也迅速,短短几秒钟而已,瞬间恢复原状,只给我留下余悸罢了。
走出CT机房,门口的护士不让我马上离开,叫我坐在椅子上休息半小时后才能离开。我很听话地坐在那里等着。
半小时安然无恙地过去了,护士说我可以离开了。
我离开CT机房,去了心电图室,医生在我胸脯的肉体上粘上许多电极,然后绑上一个心电图检测器,叫我24小时后再来这里。
我知道,这就叫“二十四小时动态心电图”,在二十四小时内,吃饭、睡觉我都得背着这台仪器。
二十四小时过去了。我拿到了两张报告单,虽然我不是这方面的专业,有着许多的不懂,但是理解文字的描述还是不成问题的。看了“二十四小时心电图”的报告单后,觉得没有问题。再看CT报告单,影像诊断是这样描述的:“冠状动脉粥样硬化:前降支近中段管壁可见以钙化斑块为主混合性斑块,管腔中度狭窄。”
“动脉粥样硬化”、“斑块”、“狭窄”这些我最不喜欢的词特别地扎眼,让我看了心跳加快。
专家医生看了看我的CTA报告单,又打开电脑上的CTA影像图片,翻翻覆覆,认认真真地翻看了一遍,对我说:“看的还是不够清楚,要确诊血管狭窄了多少必须做‘冠状动脉造影’才看得清楚。”
医生建议我住院,做一个“冠状动脉造影”,这样就可以准确看清血管的狭窄程度,在做造影的过程中,如果发现心血管确实狭窄到了需要放支架的程度,就立即植入支架。
我没有立即听从医生的建议,对医生说,我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,病情不会这么严重吧?
医生说,这种疾病就危险在患者自己没有感觉上,一旦感觉发病,抢救的黄金时间不超过二十分钟。
我知道医生所说的话不是危言耸听,对心梗病人我是有所耳闻的,人们无不“谈梗色变”。
尽管如此,我还是婉言谢绝了医生住院检查的建议。
回家之后,把病情告诉家人,到电脑查阅相关资料,询问懂医学的朋友。
最终和家人一起达成共识——必须做“冠状动脉造影”——医院去做。
接医院相对应的专家,然后预约挂号。
一切进展得如此顺利,顺利得令我难以置信。医院专家只翻了一下我的病例,就说给我安排住院检查。
医院一向是“一床难求”而闻名,今天怎么会有那么多空床位?我对医生笑笑,疑惑地问:“有床位吗?”
“有!你确定要住院,我马上给你办理。”
既然有这么好的运气,何乐而不为?说:“住院吧。”
医生很快给我开出住院单、核酸检测单、血液化验单、B超单、CT单、心电图单等等,还有一张A4纸打印的“院前检查导引”
“你马上去‘住院预约窗口’预约住院时间,一切按‘导引’上的提示一项项去完成。”医师对我说。
我按照“院前检查导引”找到住院预约窗口,在那里取号排队。两个小时后,终于办好了住院手续,交了押金,护士给我手上套起了住院手环(住院标记)。这时,我已经成为该院里的一名住院患者了。
接下来,我又按照“院前检查导引”去各个检查窗口排队、检查。一直忙碌到下午5点半才回家,第二天,医院做空腹抽血。各类化验单、检查报告单是不需要自己取的,由住院部统一拿取,因为我是住院病人。
我的手术造影时间约在5天之后。在这几天的时间里,我手腕上戴着住院手环,遵医服药,在家里晃悠晃悠。原来我住的是“日间院”。
5天后的早晨,医院,又按照“院前检查导引”找到“日间手术中心”。那里的门卫检查了我手腕上“手环”后,就放行,护士台的护士按照“手环”的编号在表册中找到我的名字,在我名字下打个√,然后拿出一套病号服装,叫我去更衣室换上。
我换上病号服装后,护士在我左手背上留下一枚滞留针。我就坐在椅子上等着显示屏上的叫号。
11点过后,显示屏上跳动着我的名字,我被叫号了。这时,一位个子不高的阿姨,一手推着一辆轮椅,一手里拿着一本病历铁夹,在叫喊我的名字。我答应着走到她面前,她从我手腕上确认姓名后说:“跟我走”!
阿姨走在前面,我在她后面跟着。
阿姨个子不高,一米五出头一点,米灰色的工作服穿在她身上显得宽松,不太合体,背后看去,要是不看那女人发型,就不知道她是女的。阿姨每走到一拐弯处、或电梯口,总要转过身来看看我,看我是否还跟着她,医院里人很多,她怕我跟丢了。也就在阿姨转身的一瞬间,我看到被大口罩裹住的脸上有一双大眼睛,眼中露出的光是慈祥的,温柔的,很像一位慈母的眼光,这样的眼光我很久很久没有见过了。
到了手术室门口,阿姨对我说:“放心吧!一会儿就出来,我在门口等你。”听到阿姨的话,我心里暖暖的。
手术室很大,里面有多台设备,都是我叫不出名字的,正中间是手术台,这手术台有点像一台很大的显微镜。患者就躺在显微镜镜头的下方,也就是放玻璃片标本的位置。
这时,手术室内有三位医生,两女一男,他们都裹得严严实实的,只看到他们的眼睛。我左边一位女医生给我身上安放电极等检测设备;右边一位女医生把我全身用布片盖了起来,头部没有盖,眼睛可以看到天花板。
“给你手臂消消毒啊!”右边的医生说着,就在我手臂上涂着消毒液。
“给你打麻药,有点疼,忍一下就好。”
手腕处一阵刺疼,我知道这是打麻药针。我感觉到有一双手在我手腕上摩挲着,一会儿就没有知觉了。
“感觉手臂有点发胀吧?”
“是的。”
手术室内很静,静得只听见我自己的呼吸声,我慢慢地侧过头去,想看看我的手臂,看看医生的操作。遗憾!有东西挡住的,根本看不到,我只好放弃窥视之心,默默地感受手臂和心脏的微小知觉。突然,我胸脯上方的“显微镜镜头”开始工作了,发出轻微的声音。原来这个巨大镜头装在一个机械臂上,镜头会自动变换角度,在我胸脯上方不停地转换着角度和高度,同时感觉右腿胯部大动脉不停地微微跳动,我误认为有东西从胯部动脉穿过似的。
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,我静静地躺着,手腕发麻发胀,感觉有东西从我的血管中慢慢的、慢慢的向内挺进、挺进-------,进入我的心脏,在心脏的血管内里游走、蠕动,是那样的轻,是那样的柔,是那样的慢,是那样的不遗余力。
右边的医生时而跟我说着话,问我感觉怎么样?我说只是右手臂发胀,其它还好。
---------
“好了!轻度的,堵了20%,放心吧!”右边的医师说。
听说“好了”,我好奇地抬起头来,见医生的手套上、手臂上、胸脯上都有好多的血迹,那是我身上的鲜血。可想而知:在割开手腕动脉的瞬间,肯定是鲜血喷射而出。见此情景,不禁打了个寒噤。
里面的一道手术室门开了,一位医生推过来一辆轮椅,叫我坐到轮椅上。我说:“没有问题,我自己会走。”
“不行的,必须坐轮椅!”
我只好听医生的,坐上轮椅。临走时我问医生:“我的心血管堵塞是轻度的?”
“是的,请放心,主任医师看了片子后会给你写报告的,你去病床上等着。”
说话间,我已被推出手术室。
在手术室最外的一道门口,我女儿和刚才送我来的阿姨已经在那里等候。我见到女儿,告诉她一切很好,心脏血管堵塞20%,女儿听了也就放心了。
女儿马上打电话,把我的好消息告诉了她母亲。
我坐在轮椅上,阿姨把我推到“日间手术中心”病房里。
我才躺到病床上,护士就过来了,她麻利地给我按上心脏监护仪,吸上氧气,挂上点滴。
我觉得吸氧是多余的,就自作聪明地对护士说:“吸氧就免了吧!我没有觉得有什么不舒服的。”
“那不行!你的心脏受伤了,需要补充氧气。”
听了护士的话,觉得有道理,我只好静静地躺着,老老实实地吸着氧气。
我在病床上躺了四个小时。这时,主治医师来到我病床前,给我述说检查结果:确诊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,属于轻度的,左前降支中段20%狭窄。要终身吃药,注意饮食、注意定时复查等等,最后,叫我办出院手续,可以回家了。
为了搞清楚体检报告单上“左前分支传导阻滞”这一句话,我前前后后花了一个月的时间,医院,找了数名专家,花了不少的精力,费了不少的周折,承受了不少的提心吊胆,幸好,检查结果不算很差,正如一位知心朋友得知我的检查结果后说“恭喜恭喜,小毛病而已,无需担心!”
确实如此,值得庆幸,快古稀之人了,身怀小恙,纯属正常,无需耿耿于怀。此等小疾完全是岁月的堆积,是生命输给时间的必然,确切地说,是我输给了时间,况且又有谁不输给时间呢?迟早而已。
在没有完全输给时间的当下,我们不应该“壮志因愁减,哀容与病俱”,应该有“莫道桑榆晚,为霞尚满天”的乐观,继续与时间跑完全程。
转载请注明:http://www.zhuanjiz.com/gbtt/8411.html